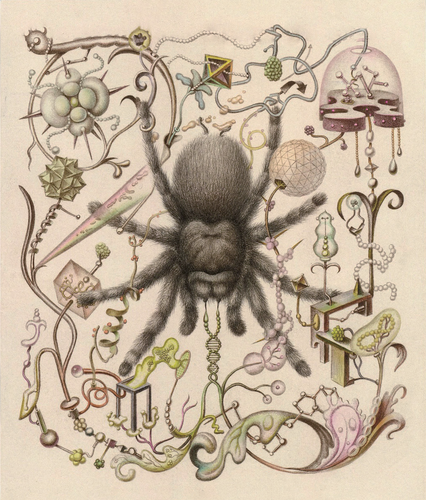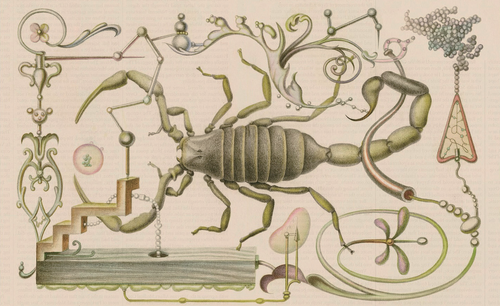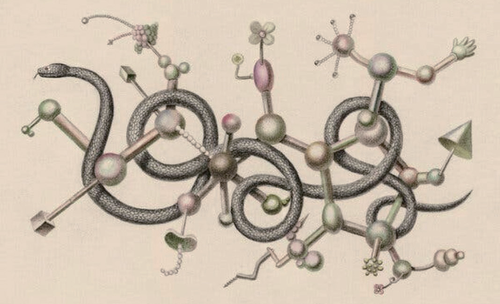对希拉毒蜥毒液的研究推动了减肥药领域的革命,但科学家认为这仅仅是个开始。
在科学领域,取得成就有两条截然不同的途径。第一条直截了当:发现问题并着手解决它。第二条听起来不太科学,或许更像是一种基于信念的方法:在默默无闻中钻研,期待机缘降临。
1980年,年轻的胃肠病学家让-皮埃尔 · 劳夫曼(Jean-Pierre Raufman)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消化系统疾病部门选择了后者。他当时的目标是积累研究经验,在此期间,他偶然结识了另一个实验室的首席化学家约翰 · 皮萨诺(John Pisano)。皮萨诺热衷于在动物毒液中寻找一种新奇有趣的激素样本——肽——并且经常通过《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向当地的昆虫及爬行动物爱好者求助。因此,大家经常会将装有疑似毒液样本的塑料袋送到皮萨诺的办公室。
皮萨诺给劳夫曼提供了一些毒液样本,供其做长期分析。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劳夫曼用这些样本做实验,看它们是否能刺激从豚鼠身上提取的胰腺细胞。到目前为止,效果最显著的毒液来自一种劳夫曼从未听说过的沙漠爬行动物——希拉毒蜥。
希拉毒蜥——行动缓慢、尾巴粗壮的陆生爬行动物——原产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南部和墨西哥北部,长着钝鼻,凹凸不平的黑色皮肤带有棕色、粉色或橙色的斑纹。它们95%的时光都生活在地下。与其南方近亲墨西哥毒蜥一样,希拉毒蜥是为数不多的会产生毒液的蜥蜴之一。它们将毒液从口腔腺体分泌到锯齿状牙齿的凹槽中。它们的下颌力量通常足以制服猎物(如雏鸟、青蛙、虫子之类)。但是,当受到威胁且无法逃脱或隐藏时,它们会紧紧咬住捕食者并刺破对方皮肤,这样毒液便会进入对方血液。这会引发剧痛和一系列其他症状,对于人类而言,这些症状包括呕吐、头晕、心跳加速、血压降低等,极少数情况下还会致人死亡。
劳夫曼对希拉毒蜥的毒液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实验后,便转而投入其他项目了。几年后,他在当时位于布鲁克林的纽约州立大学健康科学中心担任教职,并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后来,他与布朗克斯退伍军人事务部(VA)医疗中心的一个研究团队展开了合作。该中心的内分泌学家约翰 · 恩格(John Eng)对劳夫曼关于希拉毒蜥的研究印象深刻,尤其对这种蜥蜴缓慢的新陈代谢——这种蜥蜴每年仅靠几顿食物就能存活下来——感到好奇。恩格和劳夫曼联手,再次对希拉毒蜥的毒液进行筛选,并发现了此前劳夫曼未曾注意到的分子(一类肽分子)。他们将这些分子命名为毒蜥激动肽3(exendin-3)和毒蜥激动肽4(exendin-4)。
恩格意识到这类肽分子可能是一种潜在的糖尿病治疗方法。他的一些糖尿病患者需要精确调节胰岛素注射量,以避免高血糖或低血糖。而exendin-4类似于一种人体激素——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GLP-1在没有糖尿病的人体内发挥着天然的胰岛素调节作用。当我们进食时,肠道会分泌GLP-1,促使胰腺仅在血糖水平过高时分泌更多的胰岛素。该分子还可以减缓消化过程并让我们产生饱腹感。科学家曾觉得,注射GLP-1会是比胰岛素更容易、更安全的糖尿病治疗方法,不过存在一个关键问题:这种激素在血液中只能持续几分钟,很快就会被降解。但令恩格和劳夫曼惊讶的是,希拉毒蜥的类似物能够在血液中持续数小时。
恩格急切地想为这种分子申请专利,但退伍军人事务部拒绝了这个提议,因为他们认为这对退伍军人而言没有什么明显的好处。劳夫曼也放弃了,因为糖尿病并非他的研究领域,而且当时为分子申请专利的做法并不常见。
然而,恩格没有放弃。1995年,他自掏腰包为这种分子申请了专利,并利用假期的时间与制药公司联系,试图说服他们将其研发成药物。最终,他将该专利以不到100万美元的价格授权给了阿米林制药公司。2002年,礼来公司同意向阿米林制药公司支付高达3.25亿美元的费用,以获取共同开发艾塞那肽(Exenatide,exendin-4的人工合成品)药物的权利。 2005年,艾塞那肽以百泌达(Byetta)为品牌名获得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的批准,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
临床试验显示,服用百泌达和其他基于毒蜥激动肽及GLP-1研制的药物的患者,体重大幅下降。然而,制药公司迟迟未意识到这种副作用的巨大潜力。随着他们逐渐认识到这一点并改进药物配方,其影响就改变了整个社会:奥泽匹克(Ozempic)、威高维(Wegovy)以及随后的蒙贾罗(Mounjaro)、泽普邦德(Zepbound)等成为治疗糖尿病和促进减肥的畅销药物。更重要的是,许多药物似乎还具有其他潜在的益处,研究人员才刚刚开始了解这些效果。有些药物似乎对肾脏和心脏疾病有预防作用,还可能减轻大脑中的炎症,而这种炎症与帕金森病和阿尔茨海默病有关。可以说,希拉毒蜥这种地下爬行动物身上一直蕴藏着一份宝藏,人们据此研发出的药物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健康进展之一。
使用exendin-4来研制降糖药艾塞那肽很可能是首次将毒液用于改善人类的代谢功能。然而,关于这种蜥蜴的毒液中为何会含有代谢激素,人们仍然是不清楚的。事实上,几乎所有毒液的核心谜团都在于其超乎寻常的复杂性。它们可能由数百种(有时甚至是数千种)分子组成,正如2019年发表在《毒素》(Toxins)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所言,这些分子通常有多种功能,使得毒液成为“生态领域的瑞士军刀”。
然而,将毒液视为一种武器的观点低估了自然选择的丰富性。茶色疯蚁会用自己的毒液作为火蚁毒液的解毒剂。 鼹鼠和鼩鼱用毒液麻痹蚯蚓和昆虫,这样它们就能把猎物安放在自己的“食品储藏室”里,等到要吃的时候还很新鲜。扁头泥蜂用血清蜇蟑螂,能把蟑螂变成“僵尸”,使其心甘情愿地跟着它们回到巢穴,然后被它们的幼虫吃掉。蜜蜂和许多其他无脊椎动物的毒液虽然会让受害者疼痛,却不会致命,想必是为了让受害者能活下来,好告诫它们的后代及同类要避开螫针。猎蝽至少能制造两种毒液,并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使用哪一种。
有时候,将毒液中的分子重新应用于人类需求也近乎巧妙。格伦 · 金(Glenn King)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化学与药物研发部门的分子生物学教授,他首次对毒素产生兴趣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那时人们越来越担心化学杀虫剂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我们从哪里可以找到一些更环保的天然杀虫剂呢?”金问道,“回想起来,答案显而易见——蜘蛛。它们在这个领域已经深耕了数百万年。”
当金意识到许多毒液肽(尤其是小型无脊椎动物的毒液肽)会作用于离子通道时,他便将研究重点转向了医学应用领域。离子是带有正电荷或负电荷的原子或分子。离子通道就像一道道闸门,决定了哪些离子可以进出细胞,从而通过改变细胞的电压来激活细胞或抑制其活动。离子通道对许多基本生理功能都至关重要,它们与糖尿病、癌症、癫痫、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及慢性疼痛等都有关。神经系统中有大量的离子通道,细胞在这里通过电信号相互传递信息。
金对一种存在于蜘蛛毒液中的肽很感兴趣。在啮齿类动物试验中,与未接受治疗的啮齿类动物相比,即使在中风后8小时注射这种肽也能使其因缺氧引起的神经损伤减少60%。
其他实验室正在研究的应用还包括一种蝎子肽,它能精准地与恶性肿瘤(包括脑肿瘤)相结合。这种肽经过改造后能显示荧光,这样医生在进行肿瘤切除手术时,就能看清是否已将肿瘤完全切除。西雅图儿童医院研究所和华盛顿大学的教授吉姆 · 奥尔森(Jim Olson)是该项目的发起人,他表示,最终,类似的分子可能会被设计成在无需化疗或放疗的情况下直接杀死癌细胞。据贝勒医学院负责相关研究的免疫学家克里斯汀 · 比顿(Christine Beeton)说,他们正针对一种来自海葵毒液的肽进行临床试验,用于治疗某些自身免疫性疾病。在巴西,生物化学家和神经科学家玛丽亚 · 埃琳娜 · 德 · 利马(Maria Elena de Lima)正在开发一种从巴西游走蛛毒液中提取的肽,用于治疗勃起功能障碍。
用实验室设计的分子来操控离子通道是非常难的。然而,至少在毒液方面,从自然界中找到了这些分子就意味着弥补了生物学家了解某种生物如何使用其毒液与临床医生知道如何帮助患者这两者之间的巨大差距。
生物学家史蒂文 · 特立姆(Steven Trim)正是致力于缩小这一差距的人。他曾创立一家公司——毒液科技(Venomtech)——专门对外出售被分离成各种分子成分的毒液,不过后来因为资金问题倒闭了。在毒液科技倒闭之前,他收集所有能找到的有毒生物,比如蛇、蜘蛛等,并每隔几周就提取它们的毒液——蛇比蜘蛛的提取频率要低,因为蛇的毒液产量非常大。然后,他使用液相色谱法分离出不同的化学成分,并利用质谱法,根据原子的重量和电荷,对它们进行鉴定。
毒液科技的一位客户是犹他大学的生物化学副教授海伦娜 · 萨法维(Helena Safavi),她研究的是芋螺毒液的化学成分。芋螺是一种有着美丽花纹外壳的海洋软体动物。
芋螺大约有1000种,其中一些通过向鱼类、蠕虫和其他海螺注射强效神经毒素来捕食。其中有一种毒素非常强,以至于有潜水者因捡芋螺欣赏而丧命。(美国联邦政府对几十种物质的持有进行管控,这种芋螺毒液就和肉毒杆菌毒素一样,是被监管的物质之一。)在萨法维十年前来到犹他大学时,该校就已经有一个颇具规模的芋螺研究项目了。20世纪90年代初,该校的巴尔多米罗?奥利韦拉(Baldomero Olivera)教授一直在研究两种芋螺毒液,以了解它们是如何麻痹鱼类的,后来他发现它们的毒液中含有能够抑制人类脊髓疼痛反应的肽,其中一种肽最终成了名为齐考诺肽(Ziconotide)的镇痛药,于2004年获得FDA的批准。
金说,萨法维是毒液疗法领域的“后起之秀”。2015年,她与奥利韦拉以及其他14位同事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描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发现:尽管芋螺因具有神经毒素而臭名昭著,但还有两种芋螺是通过扰乱鱼类的代谢来捕食鱼类的。芋螺将含有胰岛素的毒液释放到水中,使附近的鱼类血糖过低,进而丧失行动能力。这些鱼会变得不协调,甚至可能会抽搐或昏厥,就像低血糖的人一样。这样一来,芋螺就能通过其看似嘴巴的部位将鱼整个“吞”下去。
时至今日,技术已经取得进步:化学家几乎不需要任何毒液,就能确定其氨基酸序列并合成它。甚至还有大型的在线数据库,里面包含了数百种毒液肽的序列,研究人员不用见到芋螺就能利用这些信息进行研究。“看到技术发展如此之快,我们中的一些人会感到有些伤感,”萨法维说道,“因为这使得实地考察没那么重要了。”
组织采集之旅并办妥所需的许可证可能需要数年时间,而且有些地点太过危险,人们无法前往。然而,这样的实地考察仍旧是发现科学界未知的螺类毒液的唯一途径。萨法维说:“我们有一长串的物种名单,也想要对这些物种的毒液进行测序,却无法得到它们。”与此同时,气候变化正在摧毁全球各地的珊瑚礁。许多在今天看来还可能会被找到的海螺,在她到达之前就会灭绝。“理想情况是,我们现在就能把所有东西都测序出来,但我觉得这不太可能会实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毒液研究人员肩负着重任,他们不仅要近距离目睹我们对自然界的破坏,还要见证我们正在毁灭的各种生物间错综复杂的关联。比顿说自己已经不再捏死蜘蛛了,“我们或许只触及了有用毒液的皮毛,每当我们摧毁一小块环境,里面又埋藏着多少小蜘蛛或蜈蚣呢?它们本身或许就相当于一个小小的制药公司”。 金指出,全球99%的有毒生物是无脊椎动物,它们产生的毒液量非常少,20年前我们根本无法确定其成分。同时,他也说:“我认为,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人们将会从我们闻所未闻的虫子身上提取出非常有意思的药物。”
资料来源 The New York 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