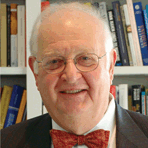“曾经由于受到夸大了的抽象倾向影响而被迫屈从的大多数物理学家,竟然那样轻易地离开了用清晰明了的语言表述量子物理学现象的道路,对此我深感遗憾。”
——路易 · 德布罗意(Louis de Broglie ),《对波动力学流行诠释的批判》,沈惠川译,1962年
一直以来,物理学为人们理解世界运行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根据。如果去问17世纪末的人们世界为何如此运转,他们会拿着艾萨克 · 牛顿(Isaac Newton)的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告诉我们这就像瓜熟蒂落一样自然且必然。这种思想被诞生于19世纪初叶的“拉普拉斯妖”演绎到极致。拉普拉斯妖熟练掌握牛顿力学,知道某个时刻所有粒子的位置和运动状态,于是宇宙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之于它都不过是数学游戏,只在计、算之间。
在牛顿力学问世后的两百年间,主流物理学界一直在该框架下解析世界。19世纪中叶,热力学奠基者之一鲁道夫 · 克劳修斯(Rudolf Clausius)提出“熵”的概念,意在描述系统的混乱程度。熵增定律给孤立系统指明了演化方向,于是宏观系统有了“时间箭头”。这与牛顿力学没有根本上的矛盾。统计力学成为联系牛顿力学与熵增定律的纽带——牛顿力学描述可逆的微观粒子演化,而熵增定律作为宏观统计规律,其不可逆的性质被部分归结于经典概率分布。然而,牛顿力学蕴含的机械决定论还是被随后出现的电磁学理论动摇。后者包含的麦克斯韦方程组描述了以“场”为媒介的相互作用形式,这已悄然偏离了机械力的图景。不过,世界仍是遵循经典决定论的。
出乎意料之事发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黑体辐射、光电效应、原子稳定不坍缩和分立光谱等一系列实验现象开始找不到自己的理论归宿。这直接促使了以玻尔-索末菲模型为核心的旧量子论的诞生。但是,某些计算结果仍与实验不符。1925年前后,量子理论取得革命性突破:德布罗意波(或称物质波)、矩阵力学和波动力学被先后提出。特别是维尔纳 · 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于1925年发表论文《运动学和力学关系的量子力学重新诠释》,标志着矩阵力学的正式创立。这是一种被广泛沿用至今的量子力学表示形式。联合国于2024年宣布2025年为国际量子科学技术年,以纪念现代量子力学的百年诞辰。
毋庸置疑,量子力学不同于经典力学。那它最本质的解释是什么?20世纪20年代,一种以“量子概率”为基础的哥本哈根诠释开始形成,后成为主流教科书对量子理论的阐释。事实上,这一诠释相当实用却丧失了对量子现象清晰直观的表述。该缺憾在一种“教科书之外”的诠释上得到了弥补——与哥本哈根诠释同时代被提出,直到1951年才被重新构建的导航波理论(后称德布罗意-玻姆理论),在近期迎来了自己的曙光(图1)。
图1 德布罗意-玻姆理论发展脉络
图2 爱因斯坦(左)和玻尔(右)
忽如一夜春风来:在导航波理论之前
早在17世纪,人们就认识到光可能具有粒子性和波动性。以牛顿为代表的粒子说和以克里斯蒂安 · 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为代表的波动说彼此长期对立,争论不休,此消彼长。直至20世纪,人们才广泛承认了光的波粒二象性,即光子同时具备波和粒子的性质。1905年,阿尔伯特 · 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为解释光电效应而提出光量子假说,重新赋予光以粒子性。1916年,罗伯特 · 密立根(Robert Millikan)通过测量电子逸出功而证实了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方程。1923年,阿瑟 · 康普顿(Arthur Compton)通过X射线电子散射实验证实了光具有动量,从而为光的粒子性提供了进一步证据。人们迫切需要一种能同时阐释光的波动性和粒子性的理论,无论是经典的还是量子的。
很快,波粒二象性被推广到所有微观粒子。1924年,路易 · 德布罗意受到质能方程和光电效应方程的启发,提出所有物质均具有波动性的假说,尝试将波动性推广到所有粒子。爱因斯坦认为这种利用物质波把波和粒子关联起来的想法对于揭开量子谜题具有很好的启发性。1925年,爱因斯坦在自己的论文中提及德布罗意的贡献。从中,埃尔温 · 薛定谔(Erwin Schr?dinger)接触了德布罗意的物质波假说并产生共鸣,之后认真思考彼得 · 德拜(Peter Debye)对物质波论述的批评——缺失波动方程导致无法真正处理波动过程。一年后,薛定谔便发现波动方程并建立波动力学。他倾向于认为波函数是物质世界的真实体现。
相比海森堡于1925年创立的矩阵力学,波动力学的表示形式为物理学家所熟悉,迅速吸引了一批支持者。然而,该理论却暂时无法解释量子跃迁现象。据马克斯 · 玻恩(Max Born)所言,爱因斯坦此前在一篇未发表的论文中提到,波或许是决定光子沿某个路径传播概率的“幽灵场”。玻恩受其启发,为将量子跃迁纳入波动力学提供了一种思路。他在1926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波函数表示电子被“抛向”某个方向的概率。有意思的是,虽然玻恩乐于拥抱波动力学,但是薛定谔并不信服玻恩的概率解释,且仍反对量子跃迁。鉴于薛定谔创立波动力学之时就极为重视波动过程的连续性,他与玻恩的立场存在矛盾也不足为奇。饱受困扰的还有爱因斯坦。他在1926年12月4日给玻恩的信中写道:“它(量子力学)还不是那么真实的东西。这理论说得很多,但是一点也没有真正使我们更加接近于‘上帝’的秘密。我无论如何深信上帝不是在掷骰子。”
在波动力学大受欢迎之际,海森堡决心重振矩阵力学。他开始关注实验,并迅速找到一个切入点:电子穿过威尔逊云室时,指示电子路径的凝结液滴比电子本身的尺寸大很多。1927年,他通过数学推导,证明位置不确定度和动量不确定度的乘积必然大于等于普朗克常数(位置-动量不确定关系),又将之拓展得到能量-时间不确定关系。与此同时,尼尔斯 · 玻尔(Niels Bohr)开始发展互补性的思想以解决诠释问题:波动性和粒子性是互补的,一个实验要么迫使电子展示其作为波的一面,要么迫使电子展示其作为粒子的一面。与海森堡不同,玻尔认为互补性才是关键,而非测量的笨拙性(即“测不准”)。在这一时期,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诠释开始形成。
图3 1927年第五次索尔维会议参与者。德布罗意(中排右数第三位)应洛伦兹(Hendrik Lorentz)之邀在会议上作了以“量子的新波动力学”为题的学术报告
江畔何人初见月:导航波理论的诞生
1927年10月,主题为“电子和光子”的第五届索尔维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邀请函上注明的“这次会议将专注于新量子力学及其相关问题”显露了真正的议题。由于量子理论的迅猛发展,邀请名单一扩再扩,最终几乎涵盖了所有量子力学主要奠基人和新生代研究者(图3)。会议共安排了五场报告,其中包含德布罗意要宣读的论文《量子的新动力学》。会议的第二天下午,德布罗意用法语做报告,概述自己的物质波理论和薛定谔的波动力学,承认玻恩的概率解释或许是正确的。随后,一个大胆的想法被提出了。
德布罗意描述出这样一种物理图像:电子(或粒子)像浮萍一样被波浪“推”着走;波对粒子起到导引的作用,因此被称作“导航波”(pilot wave)。通过这种方法,波函数不必再如玻恩所言的那样只能被赋予不实在的概率解释;电子也不必再如以玻尔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所言的那样在一次实验中只能展示出波或粒子(二选一)的性质。在导航波理论中,波函数描述了真实的物理场,波和粒子始终同时存在。
这样一番报告,不大可能获得玻尔和海森堡等人的赞赏,他们要维护被导航波理论挑战的哥本哈根诠释;也不大可能获得薛定谔的重视——他一方面忙于与哥本哈根的“矩阵派”对决,向玻恩深受欢迎的概率解释进攻,对被广泛认可的量子跃迁提出质疑,另一方面也不相信有这样的粒子。好在,在座的还有爱因斯坦。这位对量子现象的阐释方式十分谨慎的量子物理奠基人,会支持德布罗意吗?
爱因斯坦保持了缄默。实际上,这种类似经典的波场-粒子协同运动,对他来说并不陌生。1927年5月,爱因斯坦在论文《薛定谔的波动力学是完全决定系统的运动,还是仅在统计意义上描述?》中已经考虑过波函数对粒子的引导作用。然而不出一个月,他就因为一些无法忽视的问题而撤回论文:虽然粒子是局域的,但导场的作用是非局域的;如果存在超距作用,因果论会被打破。另一方面,没有理由表明波函数需要被赋予物理意义。这或许是导致爱因斯坦决定不在10月的索尔维会议上作报告的原因之一。不过,尽管在会中对德布罗意的导航波理论未置一词,他还是在几天后的讨论中第一次公开表达了与哥本哈根学派对立的观点,并予以有力抨击。整个会议结束后,爱因斯坦劝德布罗意要坚持,并说这路子是对的。
事实上,德布罗意在会上的状况要比被漠视更恶劣。他遭到了哥本哈根学派的围攻。沃尔夫冈 · 泡利(Wolfgang Pauli)嘲讽德布罗意的理论“竟然无法处理两个粒子的相互作用”。可难道哥本哈根诠释就是面面俱到的吗?很遗憾,哥本哈根学派“用强大的人格魅力和声望信誉碾压了缺乏自信的德布罗意”,而非坚实的论证。不过,导致德布罗意受重创的或许还有他自己表述不当的原因。虽然他给听众呈现出的是导航波理论,但他真正聚焦的是“双重解理论”。该理论在先前论文中就已经被提出,但当时非线性波动理论还未被发展,双重解面临数学障碍。德布罗意的弟子、法国路易 · 德布罗意基金会曾任主席乔治 · 洛切克(Georges Lochak)在《德布罗意波动力学诠释思想的演化》中总结道:“由于双重解理论存在极大数学困难,德布罗意在报告中只提到了其简化形式,即导航波理论……但失去了该因果理论的逻辑一致性。”也就是说,他退后一步,将双解合二为一。代价是露出破绽,被泡利等人牢牢抓住。
回顾第五届索尔维会议,它几乎达到了量子论战混乱状态的最高峰。不同的人用德语、法语或英语发表着不同的见解。当然,不只是语言——保罗 · 郎之万(Paul Langevin)认为其“观念的混乱达到了顶峰”。会议第三天的上午,玻恩和海森堡在两人的联合报告中激进宣称:“量子力学是一个完备的理论,无须再对它的基本物理和数学假设做任何修改。”爱因斯坦在笑。不管怎样,哥本哈根诠释(该称呼在1955年被海森堡首次使用)在本次会议后开始正式形成,并在大部分参会者心中树立起可靠的形象。虽然哥本哈根诠释的提倡者们内部仍有不小分歧,但共同基础在于玻恩的概率解释、海森堡的不确定原理、玻尔的互补原理和对应原理,以及测量导致波函数坍缩至本征态。二十多年后,在哥本哈根诠释早已深入人心之时,德布罗意-玻姆理论才终于借玻姆之手被重新提出,但想要真正发扬一种姗姗来迟的诠释又何其困难!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虽然在会议上无人能论述导航波理论是错误的,但随后一本书的问世还是给予它沉重一击。德布罗意的导航波理论认为,粒子作为波上的冲浪运动员,是可被测量的,而波则无法直接被测量,只能通过对粒子的测量结果来推测存在。在这一理论中,存在一种隐藏的变量——隐变量。它是一种真实的物理量。一旦我们掌握了关于该变量的信息(隐变量不再隐藏),我们就可以准确预知粒子的位置和动量等性质。在经典物理中,隐变量并不稀奇。17世纪,描述气体体积与压强的玻意耳定律在实验数据中被总结出来;气体分子的运动状态就扮演“隐变量”的角色。如果量子力学的隐变量理论是正确的,就表示现在的量子理论并不完善——一个更为基础的、“不掷骰子”的现实世界存在但未被发掘。然而,令隐变量支持者们大失所望的是,天才数学家冯 · 诺依曼(von Neumann)在他1932年出版的著作《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中“证明”——该论证先后被格蕾特 · 赫尔曼(Grete Hermann)和约翰 · 贝尔(John Bell)指出其可加性假设不成立——引入隐变量无法实现对量子力学的确定性描述。本就势微的导航波理论几乎被抛弃了。
另一边,爱因斯坦对概率诠释从来没有满意过。他的想法在1927年11月给索末菲(Arnold Sommerfeld)的信中表达得很清楚:“我认为,就有重物质来说,‘量子力学’所含有的真理差不多同不用量子的光学理论同样多。它们似乎都是一种正确的统计规律理论,但对于单个基元过程还缺乏充分的理解。”理论的不完善固然令人困扰,但玻尔带着众人固守哥本哈根诠释,仿佛量子物理学大厦已经“封顶大吉”,这或许更令爱因斯坦不满。他在1928年5月给薛定谔的信中写道:“海森堡-玻尔的绥靖哲学是如此精心策划的,使它得以向那些信徒暂时提供了一个舒适的软枕。那种人不是那么容易从这个软枕上惊醒的,那就让他们躺着吧。”话虽如此,爱因斯坦始终致力于“叫醒”他们。在他的诸多尝试中,最具深远影响的当数提出EPR佯谬。
1935年,爱因斯坦与两个聪明的年轻人鲍里斯 · 波多尔斯基(Boris Podolsky)和纳森 · 罗森(Nathan Rosen)合作发表论文《能认为量子力学对物理实在的描述是完备的吗?》,第一次描述了EPR佯谬。据说,罗森负责数学计算,波多尔斯基负责文章撰写。他们假设粒子1和粒子2在短暂的相互作用后,相互分离,且不再有任何的相互作用。根据量子力学,如果测量粒子1的位置,粒子2的“位置”属性就可被准确预知;“粒子2的位置”是一个实在元素,而“粒子2的动量”不具有物理实在性。反之,如果测量粒子1的动量,粒子2的“动量”属性就可被准确预知;“粒子2的动量”是一个实在元素,而“粒子2的位置”就不具有物理实在性。此外,需要注意:两个粒子分离后,对粒子1进行任何测量不会影响到粒子2(EPR认为这是对“无相互作用”的另一种表述),即与粒子1分离后的粒子2始终是同一个实在。同一个实在怎么会有两种不同的实在元素?
倘若波函数给出的描述是完备的,那么“粒子2的位置”和“粒子2的动量”这两个实在元素应该被同时包含在波函数的完备描述中。但上述分析没有得到同时包含两个实在元素的结果。最终,EPR得出结论:波函数没有给出关于量子力学实在的完备描述。在论文的末尾,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和罗森谨慎又充满希望地写道:“虽然我们已经证明波函数并不能完备地描述物理实在,但我们对‘是否存在这样的描述’这个问题保持开放态度。不过,我们相信这种理论是可能存在的。”
沉舟侧畔千帆过:重提并完善德布罗意-玻姆理论
20世纪20年代,奥本海默(Julius Oppenheimer)从欧洲游学回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研究生讲授量子力学课程。他的教学风格极有吸引力,吸引不少研究生多次重复选修。20世纪30年代的老师们普遍认为,量子力学阐释和哲学性表达在量子力学教学中是必要的。20世纪40年代,量子力学阐释的开放性探讨仍然在考试中常见。然而,到20世纪50年代,很少有老师会强调不确定原理和量子概率的解释,遑论量子力学的哲学观点;考试的侧重点也变为标准计算方法。
1942年,后来的玻姆力学创始人大卫 · 玻姆(David Bohm)在导师奥本海默的指导下,顺利取得博士学位。随后几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1951年,玻姆根据自己的课堂讲稿,出版了一本很受欢迎的教材《量子理论》。奥本海默赞赏玻恩的概率解释。因此,玻姆在书中密切追随着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诠释,并暗示玻尔对EPR佯谬的回应已经足够。不过他仍然把EPR佯谬推进了一步。为了简化教材的数学公式,玻姆将其初次推广到了离散的自旋角动量(而非上节所述的位置和动量)。玻姆版本和EPR原始版本有些许差别,前者认为两个粒子在分开后“无显著相互作用”,而非后者认定的是“无相互作用”。遗憾的是,由于政治原因,这本“在数学形式与概念诠释之间达到完美平衡”的教材在玻姆有生之年未能再版。
图4 大卫·玻姆
爱因斯坦视玻姆的《量子理论》为将哥本哈根诠释说得最清楚的一本书。这说明玻姆已经参透了概率诠释的精髓。尽管不完全认同其中的观点,爱因斯坦仍然邀请玻姆会面。这次会面对玻姆影响巨大——他开始认识到EPR观点的可取性,立即寻求并很快找到了一种概率诠释之外的解释量子力学的方法。其实,玻姆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重新发现了导航波理论(现称德布罗意-玻姆理论)。玻姆的文章于1951年7月被送到《物理评论》(Physical Review)必威体育备用地址 ,并于1952年1月发表。他在最后写道:“作者谨此感谢与爱因斯坦博士的数次有启发性的探讨。”
德布罗意-玻姆理论描述了这样一种量子世界:粒子被量子势(依赖波函数及粒子质量)导引而具有确定轨迹(玻姆轨迹);粒子始终具有确定位置;对粒子的观测结果满足不确定原理,但这种不确定来自粒子初始状态的不确定。针对著名的双缝干涉实验,该理论也给出自洽的解释:单光子面对双缝时,只通过一个狭缝,但波函数却通过双缝,分裂成实波(含光子)和空波(无光子)。一言蔽之,该理论保留波函数,引入量子势和玻姆轨迹,直观解释了量子现象。量子测量终于从波函数“瞬间坍缩”之下解脱。
德布罗意-玻姆理论是一种非局域隐变量理论。因为玻姆相信(尽管未明确指出)冯 · 诺依曼1932年的论证存在问题,并受到爱因斯坦的鼓励,所以该误论没有再次妨碍隐变量理论的发展。在看到玻姆的论文后,泡利仍坚持批评态度;德布罗意一方面指出该理论是他1927年在索尔维会议上提议的翻版,另一方面坚持认为“从双重解理论来看,导航波理论没什么价值”。自1952年至1987年,德布罗意重返量子力学诠释的战场,对周遭的怪异目光淡然处之,在探究双重解理论的道路上继续前进。而玻姆除了继续研究导航波理论之外,撰写了一系列哲学书籍阐述自己对宇宙本质的洞见。
在玻姆重提导航波理论的几年后,一个可以把量子论战从哲学范畴拉回物理实验的机会降临了。1957年,玻姆和他的学生亚基尔 · 阿哈罗诺夫(Yakir Aharonov)在一篇论文中对EPR佯谬的自旋版本进行了更多的阐述,使EPR佯谬离实验检验更近。在此基础上,贝尔,这位一读到玻姆的文章就确信冯 · 诺依曼出错了的物理学家,于1964年提出了著名的贝尔不等式。贝尔相信,爱因斯坦在期待一种比德布罗意-玻姆理论更深刻的东西,因为玻姆的理论仍像哥本哈根诠释一样,蕴含“鬼魅般的超距作用”。贝尔想知道,所有的隐变量理论都必须是非局域的吗?
图5 1982年,贝尔正在讲述他的不等式
贝尔不等式为实验检验局域隐变量提供了可能。最早检验贝尔不等式的实验由约翰 · 克劳泽(John Clauser)和斯图尔特 · 弗里德曼(Stuart Freedman)于1972年完成。另一个重要实验由阿兰 · 阿斯佩(Alain Aspect)等人完成,于1981年被报道。后续还有一系列不同的实验在弥补漏洞方面进行了多番尝试。至今为止,几乎所有的实验结果都表明:贝尔不等式可被破坏,局域实在论可能是不对的,局域隐变量也无法解释量子纠缠现象。不过,类似德布罗意-玻姆理论的这种非局域隐变量理论,还未被证明或证伪。
__________________
本文作者尚晓文是上海交通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金贤敏教授课题组博士生;窦建鹏是上海交通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助理研究员;唐豪是上海交通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教授;金贤敏是上海交通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